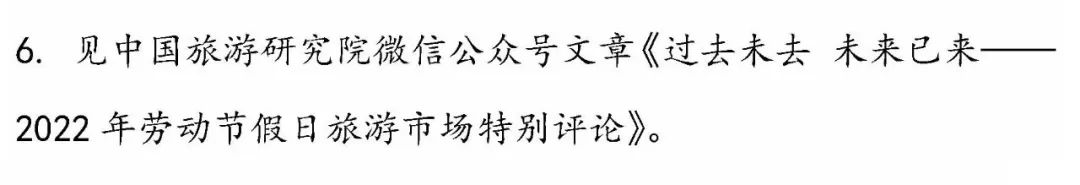应《旅游导刊》主编秦宇教授邀请,戴斌院长撰写特稿《旅游研究的培根方法与理论建构的 NOMA 原则》,原发于《旅游导刊》2022年第5期,《旅游管理》2023年第6期全文转载。院平台转发此文,以应4月23—24日在京召开的2023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主题:强化“三大体系”建设,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01 梁思成的独乐寺与培根方法
为了解读李诫的《营造法式》,通过对中国历史建筑的探幽发微而阐述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为了破除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的论断“中国和朝鲜境内一千岁的木料建筑物,一个亦没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从1932年到1937年走遍了中国的北方大地,对古代木料建筑进行野外考察和测绘。他们的第一份成果就是《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之后10年经对200多个市县的田野考察和数以千计的古建筑测绘,于1946年形成了英文手稿《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书中精心绘制的手绘图、建筑实景照片,加上极其扼要的文字,给予了西方读者一个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简洁明晰的概括性认识。1984年,该书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就获得了“全美最优秀出版物”荣誉;2015年,读库重印出版《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也已成为建筑史的经典著作1。对于古建筑爱好者来说,通过阅读文字和手绘图,也会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木建筑有概括性的了解。 与培根方法相对照的还有“笛卡尔方法”或者说数学的方法:从可靠的基础出发,仔细、缓慢地前行,一点点地探索,一点点地获得真理,像做数学证明题那样,根据定义和公理推导出定理。在科学的全盛时期,人们以为单凭理性,便能摆脱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认识一切必须了解的真理。然而,就是在最狭义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对笛卡尔方法也是没有形成共识的。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写道,“不以某种方式与直觉相连的概念,便不能产生知识;不以某种方式与概念相连的直觉,亦不能产生知识”,“无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无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 (斯蒂芬·杰·古尔德,2020)。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工程实验,还是社会科学的思想实验,我们都会使用演绎的方法。在一些初入研究门槛者眼中,演绎的方法似乎比归纳的方法要容易些,或者说看上去更像科学。 回到旅游研究的主题。在我们决定下场之前是否也需要确认手持的是培根方法还是笛卡尔方法?在正式言说之前,是否也需要去“独乐寺”驻场一段时间?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当代旅游学者来说,观察、分类和描述是需要终身练习的基本功。为此,我们需要去体验山山水水的自然环境,浸入文化遗产的叙事体系,需要深入了解旅行社、在线旅行商、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免税店等各类市场主体丰富多彩的市场探索和商业实践,更需要去大众旅游者的消费场景和活动现场,像熟悉掌心的纹路一样熟悉游客和业者的所思所行。他们中有名人政要,也有我们的父老兄弟;有国际品牌酒店的高级管理者,也有民宿老板娘和餐厅服务员;有说走就走买张头等舱机票去伦敦海德公园喂养一下午鸽子再返回香港的有钱有闲者,也有明知有陷阱也要报个低价团,哪怕频遭白眼也决不进店买东西,到了饭点拿出干粮就着凉白开下饭的老年旅游者。当田野调查的对象从物转向人、从自然转到社会时,理论、方法和手段都要发生变化,自我民族志、参与式调查和行动研究就变得很重要。 20多年前,在我撰写硕士论文《现代饭店集团研究》和博士论文《中国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研究》的过程中,自己最大的困惑是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学界与业界“隔山隔水”的问题。我熟悉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罗纳德·科斯、小宫隆太郎对企业的定义,读过松下幸之助、李·艾柯卡、比尔·盖茨等企业家的传记,却没有住过任何一家国有宾馆,也不认识任何一位总经理和部门经理,既没有环境的实感,也不了解国有饭店领导人和员工在做什么和想什么。怎么办?就得从县、市、省一级级往上摸索,由小到大,从少到多,一点点地积累人脉、案例和经验。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节点都需要付出艰辛,才可能获得点滴的实感,慢慢地就把书本上的概念、知识和理论还原到现实中,再慢慢把实践中得来的信息、数据、案例,还有人情世故,分门别类地纳入培根的“小盒子”里,以理性之土壤和灵性之文字将之培育成为自己的这一棵“知识之树”。 02 弗罗斯特的《未选之路》与走向实践的社会科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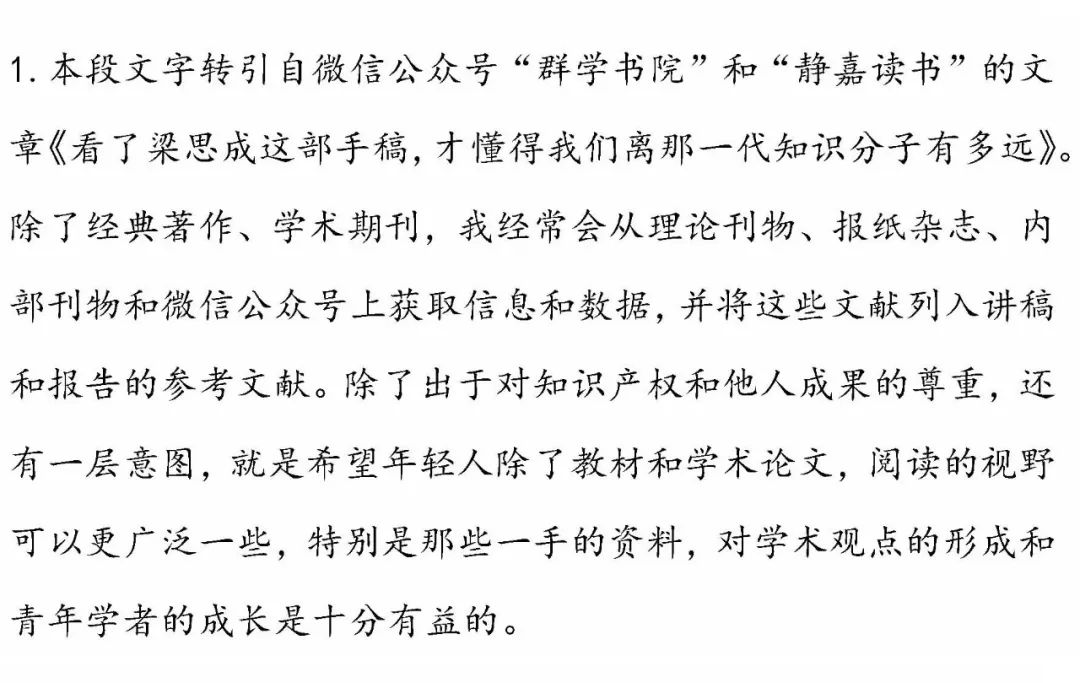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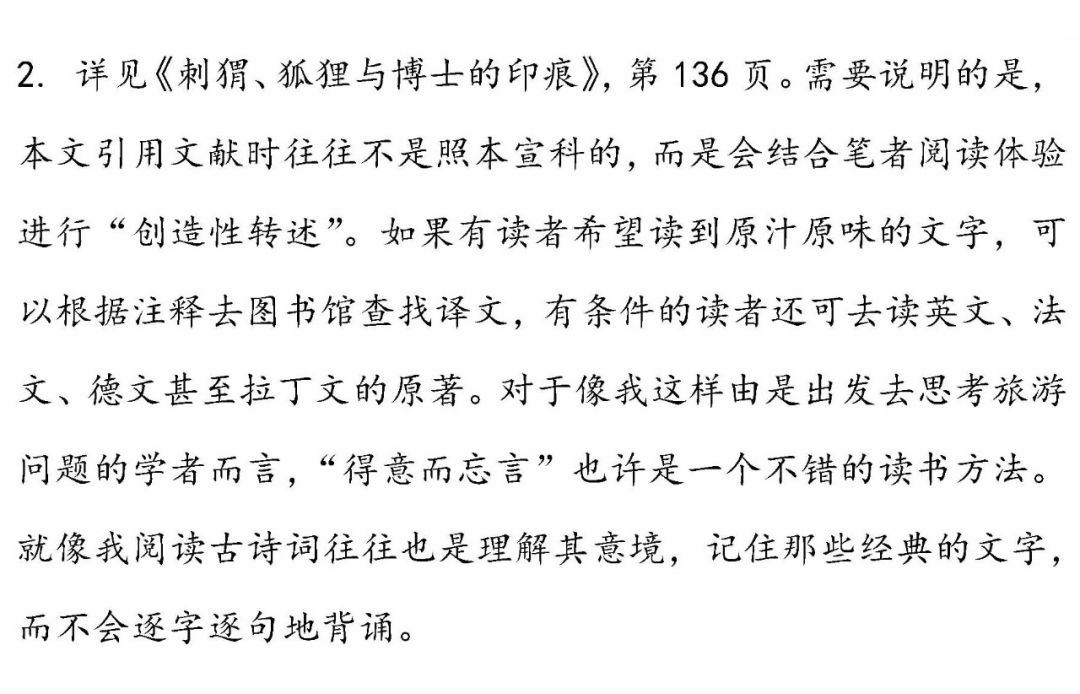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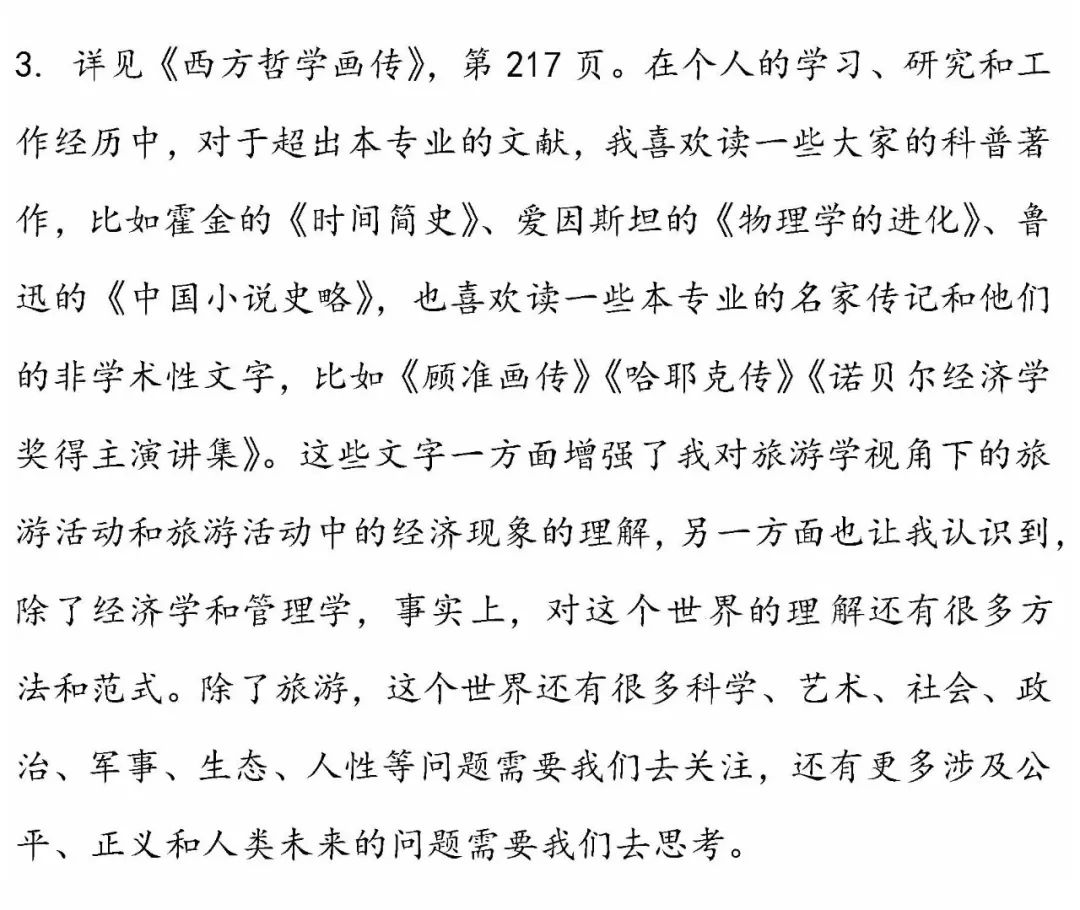
说到理性与感性,很多人应读过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orst)的《未选之路》(The Road not Taken),“黄色的森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诗人在伫立之后,“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诗人是敏感的,学者是理性的,可是哪怕艾伦·图灵再世也无法穷尽所有的信息,在成本 - 收益框架中求得那个最优解,而不得不行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总在路口彳亍,更不能坐等导师给出明确的答案。如同创业者,多数时候都不是因为看见而相信,而是因为相信而看见,只是让理想之光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任何实践都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也可能是“错着错着就对了”,但是一味地躲进象牙塔里清谈就没有风险了吗?一个想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父系思维,只能导致什么都要等待安排的巨婴行为。
在中国从事旅游研究,还是读些文史哲方面的经典文献好。不是让大家去上什么国学班,就是多读《战国策》《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史记》等,里面有国情,也有人情,有政治智慧,也有文字功底。我们不是从事古典文学专业的,不需要字斟句酌地精读,太难的或者暂时不感兴趣的就不读,感兴趣的就反复读,总之开卷有益,也可以得意忘言。我自己的阅读就是很泛的,前段时间看浦江清先生的传记和文章,他总结出人类最高情绪由歌曲而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了诗词。从诗词本体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有从原生态的民歌到文人加工过的乐府,再到可读但不可吟唱的诗词这样一个过程。认为诗高于乐府和民歌的观点,可能是对诗史和文学史的误读(浦江清,2016)。旅游研究和学术成果的认定是否也适用这个逻辑呢?我看也是可以适用的。从市场实践、行政实践和教学实践而来的制度、标准和流程,相当于民歌;学者的课件、讲稿、咨询报告、发展规划和报刊文章相当于乐府;学术期刊刊发的论文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题著作相当于诗。我们不可能越过乐府直接进入诗的阶段,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学术成果就比讲稿、课件、报告高级,那样很容易自我精英化而“内卷”。
包括旅游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由某一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一项由该理论所生发出来的研究问题,目标则是证明(少数时候也是为了否定)所设定的“假说”。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是明确说明的,也可以是未经明言的,但总是带有一系列不言而喻的立场,甚或无意识的预设。在论文导向的研究体系中,我们习惯于从文献中寻找题目,而不是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这里所说的文献主要指学术期刊,特别是中外文核心期刊上由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公开出版的专著、教材和讲稿,以及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求是》《旗帜》《前线》等报刊上的文章。更加贴近政策实践和产业实践的理论文章则很少进入研究者的文献综述视野,更不用说行业媒体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字了。不是说学术期刊的论文不重要,也不是否定科技论文的写作范式,而是希望大家阅读的视野要宽泛些,沉入基层和深入一线,想业者之所说,急业者之所急,以问题导向选择研究的课题与调查的主题。如果只是在同行之间聆听和言说,甚至内卷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论文高”,那就不好了。
事实上,由实践而非理论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更有可能是所研究国家自身的内生要求,而不是源自西方理论/认知所关切的问题(黄宗智,2021)。2008年以来,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同事致力于一边解答实践问题,一边建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无论是400余期的《旅游内参》(含特别报告),还是150余部《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和分市场与行业的研究报告,无论是旅游领域中首个科技重大项目和首个社科重大项目,还是上级交办的项目和自主立项的课题,无论是已经出版的《游客满意论》《旅游消费论》,还是正在写作的《旅游政策论》和计划中的《旅游市场主体论》,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指导思想:坚持从国情和实践出发去建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和经验出发去裁剪实践,坚持时代是出题人,学者是答卷人,业界是阅卷人;坚持服务产业,报效国家,努力成为旅游领域的“理论近卫军”和“数据特战队”。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很多时候,我和团队必须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学习和使用的理论往往源于欧美范式,以逻辑自洽和现象解释为主。“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实践总是容纳着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现象或者说悖论。这就要求当代旅游学者必须也只能根据实践自身的归纳逻辑而非理论的演绎逻辑,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经由专业训练的概念化来建构理论。
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旅游还处于学科发育的早期阶段,现在谈论大一统的形式化理论和知识外溢可能还为时尚早。只有坚持与实践同行,才能发现值得研究的真问题。只有坚持与业者对话,在服务实践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才能为大学问和大理论奠定基石。我们决不能像中世纪的哲学家那样,“只是为了彼此而写作,而非为当时的普通百姓写作。僧侣之间讨论的问题,也许唯有僧侣才真正感兴趣。哪怕你能阅读拉丁语,中世纪哲学也完全有可能不是以你为读者的” (杰里米·斯坦格鲁姆、詹姆斯·加维,2014)。也许我们可以多去看看早期希腊哲学家的著述和传记,“(他们的)广泛兴趣,与经院派哲学家的狭窄兴趣,这两者的对比令人震惊”。伯特兰·罗素指出:“德谟克利特死后,哲学失去了很多富有活力的、独立的、儿童般的热情。(经院哲学)对神学细节的这种关注,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关于天使的358个问题及其答案,是以牺牲更广泛的哲学考察为代价的”(杰里米·斯坦格鲁姆、詹姆斯·加维,2014)。当代旅游研究和发展理论必须建立在国情和实践的地基上,而不是建立在天上的月光和水中的倒影上。正如我们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学到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
03 刘欢的《心中的太阳》与古尔德的“NOMA原则”
多年以前,刘欢唱过一首《心中的太阳》:“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个更高。”没有一个人可以穷尽一切真理,也没有一个学科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怎么办?沿着一个热爱的方向前行,穷尽一切可能的知识、理论、方法和工具,由浅入深地多维度思考,终会有所成就。在此过程中,切忌东张西望和心神不宁。等到有所思、有所悟了,需要克服的就是执念,千万不能以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误的,也不能以为只有科学才是理解和认识旅游现象的唯一路径。或者说,我们需要科学,但是不能走向“科学的傲慢”。
正如科学家,也是科学史作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提出的“NOMA原则”,即科学和宗教享有“非重叠的权力领域”(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NOMA),或者说,非重叠的教导职权(teaching authorities),科学试图记录并说明自然界的事实特性,而宗教所处理的则是关乎我们生命之意义与恰当品行的精神问题和伦理问题。自然的事实根本不能指示正确的道德行为或精神意义(斯蒂芬·杰·古尔德,2020),包括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承认:科学并不是一堆定律,或者不相关事实的目录,而是人类心灵的创造,有着自由发明的观念和概念。物理理论试图形成一幅实在图景,并且建立它与感官印象世界的联系(杰里米·斯坦格鲁姆、詹姆斯·加维,2014)。在宗教缺失的情境下,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等人文科学和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学科也在行使与科学非重叠的教导职权,并与科学分享包括旅游在内的非重叠的权力领域。
如果科学家承认其事业有着不可避免的人类特性,如果人文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承认尽管科学工作带有所有的人类缺点,但是仍然具有为人类真知宝库添砖加瓦的力量,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打开二分法的枷锁,握手言和(杰里米·斯坦格鲁姆、詹姆斯·加维,2014)。如果我们承认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承认旅游是人们由于休闲、事务和其他目的而到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其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那么就必须承认旅游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在科研实践过程中,往往还需要人文学科做支撑。我们还须承认,“科学并非正确信仰的购物清单,而是一种发现世界的方法,它重视经验性的观察、度量、预测、可测试性,重视全部真实观点的绝对可修正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利奥波德·英费尔德,2019)。如果没有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内的这样看上去不那么令人舒服的思想家的努力,那么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他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有道德的政治领袖必定时时遵守道德规范,其行为必定时时体现正义和仁慈的美德。马基雅维利在1532年出版的《君主论》中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政治领袖,或君主,不必介意激起对恶德的毁谤,没有那些恶德便很难拯救城邦。他以这种方式,将道德问题与领导力分开,向建立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迈出了第一步。如果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我们不得不正视科学的局限,那些看上去自洽的逻辑、精致的模型和严格的推演,很多时候并不比经验描述和思想实验更接近真实,更不用说解决问题的功效了。
历史上的旅游教育是职业导向的,旅游研究是与旅游实践同行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之所以是行业翘楚,不是因为有多少名家大师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过多少基金项目,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与实践同行,培养酒店行业用得上、留得下的人才。早期的旅游研究主题多是服务标准与流程、食材精选与出品制作、收益管理技术、跨文化交际、消费者行为与游客满意等业界关心的话题,过去20年的经济型酒店、在线旅行商、国有旅游企业改革,以及大众旅游、智慧旅游、绿色旅游、避暑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行、旅游经济预警、疫情影响、市场复苏与纾困政策等主题,同样是政府和业界在不同阶段所关注的。这些实践导向的问题很难获得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给出的答案可能也没有期刊论文那么逻辑严谨,甚至也不是那么有文采,但是能够解决旅游实践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样需要旅游学者倾尽所有的才情和努力而为之奋斗终生。
过去的20年,是大众旅游飞速发展的20年,是旅游消费、市场需求和产业动能持续变化并向旅游教育、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不断提问的20年,也是旅游研究在构念、模型、样本和表达方式上持续科学化和精致化的20年。为每年涌现数万篇论文、上千部论著和研究报告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淖”。远方还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近处还有连绵不绝的中间学科和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经验,甚至直觉。无论自然状态有多少科学的问题,旅游权利的确立、诗与远方的向往、道德与意义的追问都是属于不同的人文领域,包括艺术、哲学和神学,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由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发明所裁定。事实上,科学从来都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论文和论著也不是传播知识,更不是表达情感的不二之选。华兹华斯的“眼泪所能表达的深沉思绪”、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能比地质、国土、生态等领域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更能够传递打动人心的真理。如果说现代科学在17世纪婴儿期处处显示出对文艺复兴人文学者的对抗,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则不应将其成功归因于某种永恒不变的“科学方法”,进而在人文社科领域保持特权和优越。作为研究领域的旅游学科和就业领域的旅游产业,没有必要,更不可能让教员和学生都向物理学所代表的经典科学看齐。事实上,不用说学生,就算是一千多所旅游院校的教员和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都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很多时候,我们得放下精英的“人设”,告诉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员或者科研工作者,如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作为语者、论者和学者的职责。5在此过程中,倾个人的才情和努力,培育大众旅游意识,守护国民旅游权利,足矣。如果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要求,我希望青年学者的文字可以科学为骨、人文为颜,风华绝代而历久弥坚,如李白那样“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陈凯歌电影作品《妖猫传》里的杨玉环,读完“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清平调》后亲自去见李白,李白却不领情说不是写给她的。玉环不恼,只是侧首说“把靴子穿上吧”,又回过头说“李白,大唐有你,才是真的了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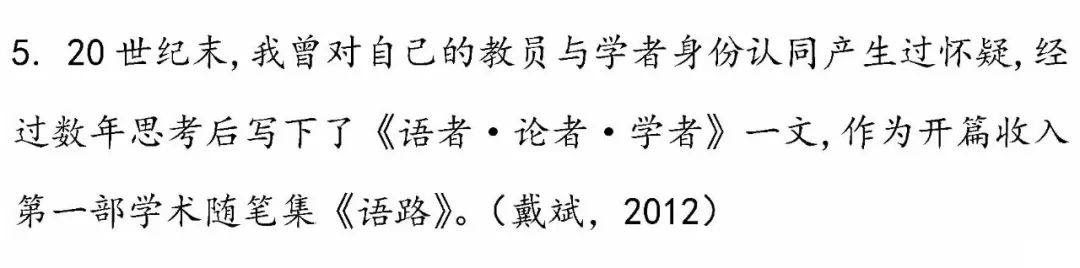
哲学和科学源于学者的好奇心和惊奇,旅游学术研究也应如是。在疫情期间我反复强调这个观点,“是旅游者定义旅游业,而不是旅游业定义旅游者”6,旅游活动、旅游业与旅游学的关系也当如是观。旅游学,还没到经典物理学的阶段,讨论自成一体的理论甚至知识的溢出,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现在需要的是兼容并蓄、百家争鸣,是问题导向、服务实践,是理论筑基、渐进突破。在旅游研究的进程中,我们需要记住卡尔·马克思墓碑上的铭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青年学者们,走出象牙塔,走出摆满了种种装置的实验室,走进丰富多彩的旅游场景,走进生动活泼的产业实践吧!青年学者们,到游客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业者最需要的地方去,把论文写到祖国的大地上,把成果应用到旅游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